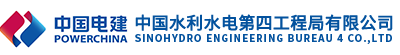【四局筑壩】光明禮贊:金沙江畔的青春在雪域之巔綻放 |
|
|
|
|
2020年8月10日凌晨五點,我拖著沉重而載滿憧憬的行李,與一同奔赴項目的18位同伴在大巴車前排起了長隊。彼時的成都,被一層薄薄的陰雨籠罩,空氣中彌漫著微微的濕意。大巴車的引擎蓋冒著白煙,仿佛在低聲喘息,預示著即將開始的漫長路途。綜合部的楊哥站在車前,聲音洪亮而有力:“大家抓緊時間放好行李上車!”就在我的行李箱輪子滾上車的瞬間,我忽然意識到:這輛搖晃的客車,正載著我駛向人生真正的成人禮。 高原上的燈火 車廂里飄著陳年煙草與皮革混合的氣息。手機信號隨著海拔攀升時斷時續,車輪碾過最后一道山梁時,儀表盤上的海拔表跳到了4250米。車窗外,八月的折多山籠罩在鉛灰色云層里,忽而落下豆大的雨點,忽而騰起乳白色山霧。沖鋒衣在濕熱與陰冷間反復切換,窗縫滲入的水汽將地質圖邊緣洇出波浪紋。當車輛駛經理塘,烈日突然沖破云層的束縛,耀眼的光芒瞬間灑下,紫外線如利箭般穿透玻璃,刺得我皮膚發燙。楊哥輕嘆一聲:“這地方的天氣就像孩子的臉,說變就變,曬得脫皮和凍得感冒,往往只隔著一頓飯的工夫。”果不其然,傍晚轉場時,狂風呼嘯而起,卷著冰雹如子彈般砸向車窗,發出“鐺鐺”的脆響。后排那個從黃淮平原來的姑娘大概是第一次遭遇這般場景,睫毛上凝著將墜未墜的冰晶,細弱的嗚咽混著便攜氧氣瓶的嘶鳴,像是剛學會啼鳴的雛鳥撞上了雪崩的余韻,車廂里彌漫著緊張與不安的氣氛。 當暮色吞沒最后一絲天光時,大巴車正碾過318國道最后的彎道。歷經十二小時顛簸的車窗上,不知何時凝起了薄霜,我抬手抹開霧氣,正撞見遠處躍動的燈火——巴塘縣城的輪廓在群山懷抱中浮現,而最明亮的那簇光暈,赫然是辦公樓頂“拉哇水電站項目部”的霓虹。 隨著距離漸近,樓前晃動的影子逐漸清晰。七八個身影在臺階前攢動,不知是誰先發現了車燈,剎那間此起彼伏的向我們揮手。當我們拖著酸麻的腿邁下車門,工程部的幾個小伙子搶過最重的行李箱,快步向我們的住宿樓走去。穿過貼滿歡迎彩帶的走廊,項目部食堂早已備下了熱騰騰的飯菜迎接我們。那一刻,所有的疲憊仿佛都被這溫暖的飯菜和真摯的笑臉融化,化作心底一抹踏實而明亮的光。 金沙江上的水電站 第一次進入施工現場那天,總工程師的黃色安全帽上沾著新鮮泥點,像枚勛章斜扣在鬢角間。激光筆的紅斑在沙盤模型上游走時,我看見他手背凸起的血管虬結成金沙江支流,隨講解節奏在皮膚下奔涌:“導流洞施工已突破關鍵巖層,日澆筑量達到5000立方米......”紅點突然凝滯在碾壓混凝土重力壩的剖面結構上,握著激光筆的指節泛起青白。 震動平臺突然啟動,模擬塌方時地面開裂的觸感從腳底竄上脊椎。VR眼鏡里墜落的鋼筋在視網膜殘留綠色光斑,與二十米外真實工地傳來的金屬撞擊聲產生詭異共鳴。安全體驗館的智能沙盤正循環播放基坑開挖全息影像,而真正的建設者在模型之外,用結繭的掌心丈量著橫斷山脈的脈搏。 暮色四合時,我隨新同事憑欄而立。十萬大山在殘陽里浸成水墨剪影,而山坳間卻躍動著現代文明的脈搏——反鏟挖掘機的探照燈如螢火蟲群般明滅,三十余臺渣土車在九曲回腸的盤山道上游弋,車燈串聯成一條吞吐天地的金色游龍。總工程師的手指劃過藍圖上的等高線:"當2026年投產之時,這里每年將注入90億度清潔電能,相當于在高原種下4.7萬公頃云杉,更將為藏地300萬家庭點亮現代之光。"晚風掠過發梢,我忽然讀懂那些穿行在海拔3000米的身影——他們正以鋼筋混凝土為筆墨,在雪域之巔鐫刻下中國建設者的擔當,為這個時代交付一份關于光明的莊嚴承諾。 成長褶皺里的暖光 泛著冷光的藍色文件夾落在我桌上時,恰好接住了一縷巴塘的晨光。分包合同上密密麻麻的條款還在眼前打轉,黃主任的鋼筆已經敲在了我的工位隔板上:"小趙,把合同邊界條款逐字篩三遍!"這位將黨徽擦得鍇亮的老經營人總像臺精密儀器,筆挺的工作服口袋里永遠別著紅藍雙色批注筆。對于剛出校門的我們,雖然他的批評總像手術刀般精準剜出紕漏,但在例會上,部門的每個年輕人都攥著被他用紅筆改出繭子的筆記本,異口同聲說那是成長最快的"武功秘籍"。 推開總經濟師的辦公室門,便見張姐舉著計算器當指揮棒,這位笑起來眼尾的細紋會漾成月牙灣的女領導。“小趙同學又來取經啦?”她總這么打趣,順手從抽屜摸出包牦牛肉干,“帶回去當夜宵,別把咱們未來棟梁餓瘦了。”她像自帶陽光特效,工作時能蹲在我們工位上手把手教組價過程,團建時又豪爽地跟小伙子們劃拳。我們總說她很像媽媽,她聽見了也不惱,反而托人從成都捎來冷吃兔,說要把“孩子們”養得跟高原格桑花一樣結實。 如今翻開那本包漿的筆記本,仿佛還能抖落出當年的牛肉干渣子。封底處,一行褪色的小字映入眼簾。那是多年前一個集體加班的夜晚,黃主任說的:“不經一番寒徹骨,哪得梅花撲鼻香。” 多年后,那些曾穿透車窗的紫外線、砸在安全帽上的冰雹、合同條款間暈染的晨光,都化作高原群星般細密的成長印記。此刻萬家燈火如星河傾落峽谷,我忽然明白,當年楊哥說的“成人禮”并非某個瞬間的加冕——當我們的腳印與前輩們的足跡在混凝土里重疊,當圖紙上的等高線化作點亮藏地的光河,這場橫跨山河的接力,早已讓青春在雪山與江流的見證下,完成了最莊嚴的淬火。夜色中的霓虹依然在辦公樓頂明滅,像永不熄滅的火種,而更遠的天際線上,又一批載著行囊的大巴正碾過新雪,將中國建設者的光芒送往更高的云端。 ?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